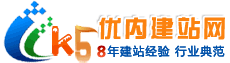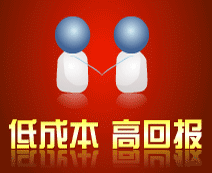我的同学X君适值壮年,风华正茂,优越感极强。他的生命并没亡去,我却不能不为他先作悼文,并非因为他精力旺盛、正当其时的机体,而是因为他在城管这个岗位上失落已久的灵魂。
大学时代,我们同在中文系,同自大巴山深处,又因他的“孤家寡人”与我的“人皆可友”,我们成为好友。当时中文系同级两个班,还有三个像他这样的形影相吊者,虽都落落寡合,却都与我友善。我虽相信“古怪人必有古怪能”一语,却更相信“人人都有一个博大世界”,故无论看谁,都觉得奥妙无穷,诚善可期。后来这三人都读完硕士,一个博士也已毕业,一个正待读博,一个热衷于做律师。
他们之所以“孤寡”,原因有三:特立独行,视他人为粪土,视自我为英雄;自私自利,唯恐他人有机可乘,唯恐自身利益受损;邋里邋遢,才识平平,多是他人嘲笑与奚落对象。X属第三类,又一直偏着头,双目暗淡无光,全身骨架随时都像要垮下去,故没人把他当一回事。他一有心事就来和我倾诉,我不待听完,大家便已坐到校外的小酒馆。
至少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其一是他看见C君练字,不禁放言:“我去当个书法家,倒也容易;如果你也想练出毛笔字,则必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蛋还难!”此语一出,即致C君自尊心大炽,后来真个自行造就成为书法家;只是他自己,至今仍和我一样写不好钢笔字或粉笔字。其二是他问我,“你既研究《周易》,能否为我算算某某主义与运动在十年后的命运?”我依言起卦,结论是十年之内尚有余地,十五年之后就很难说了。他认同我的判断,因而不再深读相关著作或“宣言”。
毕业后我去省城从事教育,他回大巴山老县城做了城管。当然他不是一般的城管队员,而是在城管办的机关搞宣传。他曾对我说,由于自己老成持重,相貌堂堂,那些摊贩与三轮车师傅多把他当作城管办主任。我回老家时曾拜访他,发现他们的主任是个“文人”,爱好文学,出过一本散文集;因兼任县级市政府秘书一职,故自称是“这个级别最年轻的官员”;又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餐馆,X带我来此就餐时,不仅摆出华宴,还请主任及一帮随员作陪;主任亦亲口向我暗示,他在省城某大型娱乐场所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他在本城所管两个领域的办事人都要来在这里就餐。
毕业后我们第二次见面,X已是宣传科科长,手下至少有一个“兵”。他当我面吩咐此“兵”的语气语调,即如他们主任吩咐他的语气语调。我们出门坐车,都不需要付费。用他的话说,这些车师傅都归他管。他的私人经济还不十分宽绰,所以在上班之外,还搞了个经营啤酒的项目;其中第一供应对象,即是他们主任经营的餐馆。他用自己的摩托带我出去兜风,我们还能一路聆听江水,欣赏奇石,采摘杜鹃,自然也谈谈理想与事业。
多年后我们再见,这是在春节前夕,我历经重重变故,回头准备和他交流心得。他们的城管办已经跃身成为城市管理局,办公地也从原来的破楼搬迁到一栋新楼。我刚上楼梯,即见他与一群人鱼贯而出。握手之后,他叫我跟他们一起出去。我问去干什么,他说出去打牌,“如果你不想打,你就看会儿电视,我陪他们玩几把,然后就和你溜开。”我说我时间很紧,只需和你单独谈几个问题。他叫那群人先走,随即带我坐进一家咖啡馆。
我没先问他的近况,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让他知道他从没听说过的一些震撼性信息。我很平静的叙述有关变故的前因后果,最后说到人类及其每一生命都必须面临一种事关危安的选择:谁能选择正义与良知,谁就能够得救,否则往往只有自毁一途。他躺在沙滩椅上,双眼似闭非闭,全身悠悠晃动,如同摇篮中的婴孩。我想他能耐心听到现在,心窍必定能够打开许多,于是我说,“现在我诚心诚意请你做一个选择,它并不需要改变你的现状,却必定能够奠定生命美好的未来。”
他侧头问我,“说完了吗?”我说是的,“这次我就为此而来,为你善念与神性的复苏而来;我们是同学兼好友,我不能不让你明白生命的真实处境与自救出路。”他长笑而起,说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坚信你是在对我撒谎,尽管你说得都像是有根有据;而且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也要劝你赶快回头,不要再在一条老路上走到天黑。他优雅的呷一口咖啡,继续说,“你看你这几年都折腾了些什么,不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还想迷惑像我这种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我说我的许多作品,如果你乐意阅读,说不定可以改变你些误会,并于你真正有益。他说不必了,办公室的电脑不适合拷贝,家里的钥匙又没带在身上。
饭后我们到护城河边散步,他开始讲述他这几年的历程。原来他已兼任两个科长的职务,可能下一步就要做副局长。他们每天没甚正事,所以上班报到之后往往都要三五成群的开了公车出去打牌。他工作岗位的收入不是太高,但他管辖了几个广告牌位的出让权,每年都能带进十几万。他提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们的城管打伤一个学生,结果几千学生群集而来,当夜将他们的办公场所砸得稀烂。他不曾目睹,然而万幸的是,当天下班时他居然将一撂重要资料无意带回家;倘若这些东西被烧或被曝光,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我问:你们是否有过反省?他说反省从来与城管无缘,我们一直如此这般派作,永远都不会觉得有何不妥。
我问他还读书吗?他说几乎不读。我问他还像当初一样思考哲学问题么?他说如果再思考,他就一定变成大众眼中的精神病。我问他是否愿意努力想一想生命的终极问题,比如,倘若我说的一切都将应验?他说即使应验我也不怕,何况绝不会有应验的可能。我说,至少善良与真诚,你总该多少保持一些。他复大笑:你今天说了这么多,而我至少不会泄密,莫非这还不够?我决定改道去看我的高中老师,遂与他作别。他挥手叫来城管的公车,说要送我到车站。车上挤满许多人,都是城管们的家人或亲人。
后来我曾想寄给他一套我的作品,但我旋即放弃。不是我要放弃挽救某个沉沦已久的灵魂,而是他早已魂不守舍,支配他一切言行的,只是城管们的思维与观念,这与苦心人的衷肠、有志者的抱负及清醒者的智慧,都远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