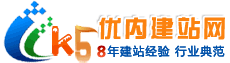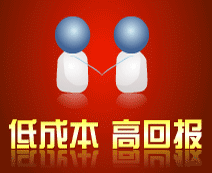大脚奶,因为脚大,大伙都叫她大脚奶。我认识大脚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那几年,在我们肖关镇经常会看到一位个子很高的老太婆在街上晃荡。那时候,她已经快奔上七十岁了。穿着一身宽大的衣服,因为她个子高,人就显得有些瘦,衣服穿在身上就不怎么合体,给人的感觉很宽松、很宽大。特别是她的衣服袖子总要长出半截,常常遮住了半只手,裤腿也很长,臃在脚面上。夏天的时候,她还喜欢敞着怀,很黑很旧的布背心里显出她那两只不怎么丰满的乳房,随着走动的脚步也在晃荡。虽说快七十的人了,头发还很黑很浓,像所有的农村老太婆一样,不怎么整齐的绾在后脑勺,用黑线勾成头发络络罩住。最显眼的是她的两只大脚,与她同年龄的女人都是小脚,而她是大脚,她的脚和她同年龄的男人一样,穿鞋最小也要四<三码</st1:chmetcnv>,可那时候,因为穷,农村人是用布或条绒做成的布鞋。大脚绅士的她就穿一双黑条绒鞋,大母脚趾头还常常露在外面。她的脸庞很大,眼睛也很大,看人的时候,眼睛睁的更大,嘴唇厚厚的,略微显得有些黑。她经常在街上走,如果你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个老头,只有你正面看才知道她是个老太婆。
文化大革命前那阵子,各村都有贫协主席,大脚奶可能是苦大仇深,被贫下中农选为我们村的贫协主席。虽说她快七十岁了,不属于队上的劳力,但她毕竟是干部,除过开会,还管村上的一些事。她当时负责我们镇子上的卫生,每天早晨、中午或者下午,她都要从镇子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北头走到南头进行巡视和检查。她检查的时候,嘴里总会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她因为辈份大,绝大多数人都叫她大脚奶。早晨她迎着东方的黎明,朝霞把她染成了金色的,她把东家门敲一阵,骂道,这是哪个狗日的熊娃把尿泼到街道上,比狗尿都难闻。她又去打西家的门,大声骂道,二娃子,你两口子狗日的还睡觉,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还不起来,肯定是昨晚你狗的×乏了,起不来。一时间,里面传出回声,大脚奶,干脆给你找个老汉吧,省的晚上睡不着,起这么早。大脚奶会骂得更凶,她说,我看你大没老婆,给我当老汉吧。她就这样骂着走着。她发现路边队里莲花白上不知被谁尿了一泡尿,她骂道,喂,各家各户都听着,昨晚谁往菜地尿尿,哪女的不怕莲花白把你×了,男的把哪求给烂了去。中午,她顶着烈日或是冒着狂风,走到街上高喉咙大嗓子地喊,各家各户,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注意听着,从今天开始,卫生大扫除,各家把各家门前的杂草铲尽,把自个儿家的苍蝇灭掉,给老鼠把药下好,狗日的懒得不动,全队给你娃开批判会。黄昏,大脚绅士披着一身晚霞又在街上晃荡。她遇见谁家娃娃没洗脸,就会骂几句,你狗日的娃连脸都不洗还当红领巾,嘴都脏成屁股了,脸上的垢痂有一铜钱厚,你是谁家娃。说着强行拉到街东头的涝池边里去给洗脸洗头。那时候没有肥皂洗头膏之类的东西,她就用涝池边的灰草草拧成汁给娃娃们洗头。她碰见谁家娃的衣服脏了,她也会骂一阵。她说,你看你狗日的碎熊,把衣服穿的像牛嚼了,皱里吧叽的,脏得像月娃子的尿布。有时候,村里有两口子吵架,她会凑上去说,狗日的打架的事,硬要吵嘴。指着男的说,你把你媳妇外狗日的往死的打,打死我去抵命,两口子会立即停下来喊她大脚奶,她板着脸说,别叫我奶,我没有你们这丢人现眼的孙子。那一年,我们村里的地主分子王一虎挨了批斗,躲在没人处哭。大脚奶知道后跑去骂,你狗的哭啥哩,有啥哭的哩,你还是地主分子,地主分子叫你枉当了,眼下就是这么个形势,这是搞运动,搞运动不批你斗你,批谁斗谁?有啥哭的哩,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来,不批地主富农,批我们贫下中农不成。几句话说得王一虎由哭转笑。说,任主席,您就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她说,啥任主席,狗屁主席,叫我奶,大脚奶。
听人说,大脚奶就年轻时的容貌,可以嫁个有钱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穿绸子、披缎子,可偏偏是她的那双大脚把她害了。她亲口给我讲过她的身世,她说,她一生下来,她妈就断了气,长到三岁的时候,她爸也死了,她就成了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到了裹脚的年龄没有人经管,她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大脚。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高挑身材,风摆杨柳,毛乎乎的大眼睛能把男人的魂勾去,一双大奶子男人们见了就站不稳。你说,哪个男人不想娶我当老婆,可人家往你脚上一看就摇头走了。她说,旧社会女人家都是一律的小脚,脚越小越好看,书上不是叫三寸金莲吗?那个潘金莲,西门庆就是爱上她的小脚才把武大郎害了,娶她为妻。她说,旧社会女娃十三四岁就嫁人,我长到二十岁还没人要。后来,村里的老光棍陈发祥娶了我,她比我整整大了二十岁,按说,他给我当爸都成,可他那个苦命鬼,把我娶进门不到五年就害了痨病死了。她说到这里,脸上的神情有些黯然和伤悲。她说,都怪我这双大脚,我要是小脚,现在至少是子孙成群,儿长女大了,不像现在孤身一人。大脚奶给我讲到这里,她不愿往下说了。关于她的一些故事,还是后来我几次从大脚奶嘴里讨出来的。
大脚奶说,她三十岁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处女,你知道吗?就是和男人没有睡过觉。她说,她的那个老男人不行,他是个阉驴,不能干那事。不能干那事他就自卑,瞧不起他自己,他连摸一下她都没有。那时候,她年轻,不能干就不干了,可那老男人死了那几年,她有些守不住,白天忙还可以,可到了晚上,她寂寞,女人没有男人的日子难熬。她说,再难熬也得熬,她把一碗铜钱撒在炕上和地下,黑着灯爬下去摸,等她一个不剩的摸完铜钱,夜也深了,她也人困马乏了,不然,她会一夜一夜地失眠。她说那满满一碗铜钱,几年下来,被她摸得明光明光的发亮。
大脚奶说,她三十岁那一年,遇见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叫王树和,四十多岁,人也长得精干。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货郎,他挑着一副担子,手里拿着一只拨浪鼓,走村串户的卖货,担子里挑的都是一些针头线脑、五色颜料、洋布袜子和洋火之类的货。他把拨浪鼓摇着“咕咚──咕咚”的响,嘴里叫喊着走东家进西家,就像《红灯记》戏里那个磨刀子磨剪子的人一样。她说,说起来也是缘分,那一天,王树和挑着货郎担子刚走到她家门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王树和跑到她家的门洞避雨,她拿眼睛一瞅,看见王树和被雨淋成了落汤鸡,全身没一处是干的,冷得在打颤,她心里不忍,跑出去把他叫到了屋子里,拿出她那个老男人留下的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天也黑了,雨还在下,王树和也偏偏病了,发开了高烧,昏迷地怎么也叫不醒。就这样,王树和在她家住了三天,他侍候了三天。等王树和病好了那天,王树和拿眼睛瞅她,她也拿眼睛瞅他,这一瞅,瞅出了事,她和王树和过在了一起。
大脚奶说,这都是缘分。这男人和女人找意中中人,你去找,你找不到,全凭碰,她和王树和就是碰在一起的。她说,要是王树和那天不避雨,她就碰不到,就是避雨,不是在她家而是在其他什么人家,她也碰不到。她说,要是王树和没有病,他避一会雨,雨一停,他就会走人,可他又偏偏病了,病得很重,走不了人,就睡在她家,他要是没有病,她也碰不到。她说,要是王树和不瞅她,她也不瞅王树和,她也不会和王树和在一起,可偏偏他瞅我,我瞅他,他瞅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像闪电一样亮了一下,她也感觉她的眼睛也像闪电一样亮了一下。这闪电碰在了一起,冒出了火花,这火花把她的心照亮了,她当时就感觉,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男人,她要找的人就是他,她和他的生疏、陌生一下子都变了,她好似以前就认识这个男人。她说,她当时问王树和,你不嫌弃我脚大?王树和说,不。她说,你愿意做我的男人?王树和说,是。她说,我还没有和男人睡过觉。王树和说,我知道。
大脚奶说,就这样她和王树和成了两口子。白天王树和走村串户的去卖货,晚上回来。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王树和出事了,他被国民党的民团杀了,民团头子王二虎把他的心肝肺挖出来炒的下了酒。大脚奶说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脸都成了黑的,眼睛里冒着火,拳头捏的咯吧响。我知道,她是仇恨那个王二虎。她说,那一天晚上,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很黑,刮着北风,风把地上的土刮起来乱飞,把树枝吹得摇摆,把家里的门窗吹得哐当哐当直响,她的心有些慌,也有些怕,就在她心慌害怕的时候,那个王二虎骑着一匹枣红大马,领着二三十个民团士兵冲进了她家的大门,还没等王树和穿衣服就被五花大绑押到了三关镇。王二虎说他是共产党的探子。
大脚奶说,现在她回忆起那天的事,她心都疼,眼前就冒金花花。那一天,晚上吹了一夜风,天一明就下起了毛头大雪。天冷得出奇,又接近年关,这一天镇上有集,人特别的多。王二虎把王树和绑在民团院子里的树桩上要进行处决。她说,这处决不是枪毙,也不是砍头,而是王二虎要亲手把王树和的心脏和肝脏挖出来炒菜下酒。王二虎原先是一个土匪头子,后来当了民团团长,这人杀人成瘾,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牛眼睛,一脸凶相,人都叫他牛魔王。她说,那天她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她亲眼目睹了王二虎挖吃王树和的心肝肺的全过程。王树和被绑在一根树桩上,除穿一条裤衩外全身暴露,一个民团士兵端了一盆清水往王树和的胸膛上抹了抹,又拿出一瓶老白干往王树和身上洒了一遍。王二虎拿着一把牛耳小刀,狞笑着向王树和的胸膛伸去,一下就把王树和的肚皮割开一条口子,心肝肺完全暴露在外面,王二虎又噌──噌几下割下了王树和的心肝肺,用刀子挑着放在了他面前的案板上,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做饭师傅,用刀很快地切成了小块,然后下到案板旁的锅里炒了起来。大脚奶说,这过程她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一点虚假都没有,王树和的心肝肺炒好后放在了王二虎面前的饭桌上,王二虎叫来几个民团的小头目,喝酒划拳,把王树和的心肝肺当下酒菜。她说,当时围在旁边的人全都呆了,一齐低下头不敢去看,那可是世界上最残忍、最毒辣的一幕,这情景就像烙铁印在了她的脑子里,永远都抹不去。大脚奶说,当王二虎向王树和下刀子时,王树和不屈不挠大骂王二虎,给王二虎唾了一脸口水,当时他只能这样,他想用手打,手被绑着,他想用脚踢,脚也被绑着,只有嘴没有被堵。当王二虎把王树和的肚皮划开后,王树和先是疼得头上冒着汗,然后脸上的肌肉就扭曲变形,再然后脸就变成了黄的,先从额头一直黄到下巴上,黄的像一张黄表,一点血色也没有了,最后头歪向一边,就在这头歪向一边的时候,王树和还拿眼睛在人群里寻找她,当她刚接触他的目光的一瞬间,王树和咽气了。她说,这一目光也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消失。
大脚奶说,她当时真想从人群中冲出去和王二虎拼命,几个乡亲们硬拽住她的胳膊,她死活都不能动,她想张嘴骂王二虎,乡亲们又用手捂住她的嘴,她同样死活喊不出来。她说,那是一九三五年冬天的事,那一年,她刚好三十五岁。杀害王树和后,王二虎扬言要她给他当小老婆,她被乡亲们藏了起来。大脚奶说,也真是应了古人一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要不报,时间没到。三天后,王二虎的人头挂在了我们镇的南门上。王二虎的心肝肺同样被炒成菜放在城门楼底下的一张桌子上,一百名民团士兵全部被俘虏。只是那个给王树和身上泼水洒酒的和炒心肝肺的大师傅在杀害王树和后的当天晚上就逃跑了。她说,她知道这一消息,跑到镇子上去看,她望着王二虎那颗人头,把王二虎心肝肺炒成的菜全部吃了下去,然后她就嚎啕大哭。她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也正好镇上逢集。刚才还红日当头,她放开嗓子一哭,刹那间一阵狂风四起,之后又有一股龙卷风,生生的将王二虎的头卷上了天,在空中呼──呼地打着旋转,最后落到了杀害王树和的那根木桩旁。王二虎的人头被摔的脑浆迸流,眼睛珠从眼眶里跳了出来滚了老远,两只野狗三下五除二就将王二虎的人头吃了个一干二净,最后只剩下些头骨。街上好多人都跑来向王二虎的头骨洒尿。大脚奶说,你不信,洒在王二虎头骨上的尿流到镇南面的涝池,一时三刻涝池都淌满了。
大脚奶说,王二虎杀人家共产党的交通员,人家共产党的游击队当然不会放过他,第三天就把他杀了。听了大脚奶的故事,我感到惊心动魄,后来我又查看肖关镇史,果真,镇史上记载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我敬佩王树和为革命献身,仇恨那个王二虎,也对大脚奶的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
就在我和大脚奶见过面之后的半年,大脚奶被红卫兵当作叛徒揪出来批斗,她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木牌,木牌上写着“大叛徒任大脚”。被红卫兵押着游街,别的这分子那分子个个都低着头,唯有大脚奶昂着胸,抬着头,样子很神气,也很滑稽。我亲自观察过一次批斗大脚奶的大会。红卫兵说,只准老实交代,不准狡猾抵赖。大脚奶说,我没有啥问题,交代啥。红卫兵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她说,灭亡就灭亡,省得挨批斗。红卫兵说,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她说,我不是叛徒,我也没有乱说乱动。她说,她和王树和结婚那几年,她根本不知道王树和是地下党,还是交通员,她也没有向敌人告密。红卫兵说,你没告密,敌人怎么知道王树和是地下党?她说,那你去问王二虎。红卫兵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她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后来,我又到街上看到一副漫画,把大脚奶的脚画得比身子还大一倍,用尽了诬蔑之能事。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大脚奶遭到批斗后,尽管表面上表现的很镇静自若,可她内心极其痛苦,她想三十年前她躲过了敌人的劫难,免于一死,今天,她却避免不了自己人强加给她的罪行,这社会怎么啦,阴差阳错。于是,她想到了死,她先是选择了上吊,结果当她刚用双脚把凳子蹬倒时,嚓一声绳断了。她又选择了喝药,她把老鼠药喝了整整一包,可等了半天,她还依然如故,面不改色,心不跳,她意识到这老鼠药是假的。她又选择了跳井,听人说跳井要先下头,她就将头伸向井口,结果两只大脚顶在一起卡在了井口,上不去,下不来。这时,走来一个人,就是那个受到批判的地主分子王一虎,对她说,上来吧,别这样想不开。她说,帮我一次忙,把我的双脚分开。王一虎说,你是嫌我罪还轻,你死了不要紧,把我害了,我也活不成。上来吧,说着把她从井里拉上来。于是两人就在井口有一段对话。
王一虎说,你还叫大脚,你把大脚枉当了,啥路不该走,走这条路。
大脚奶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我不是叛徒,他们说我是叛徒,我冤枉啊。
王一虎说,千不怪,万不怪,都怪你那双大脚,大脚把你害了,害成了这样。
大脚奶说,这话怎么讲?
王一虎说,你要不是个大脚,而是个小脚女人,你长得这么漂亮,这么水灵,不愁嫁不下个好男人。你要不是脚大就不会嫁给那个老男人,也不会嫁给王树和,不嫁给王树和,就不会有人说你是叛徒,没有人说你是叛徒,你也不会去跳井,去喝药,去上吊,对吗?
大脚奶不语。
王一虎说,要我说,这都是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还是好好活着吧。
大脚奶不语。
王一虎说,你说你冤枉,老子我比你还冤枉,他们凭啥收了我的地,分了我的房,还要批判我。
大脚奶像蝎子蛰了一下,猛跳起来。大声说,王一虎,你想翻案,想复辟?我要向造反队告你。
王一虎吓得连连告饶,大脚妹,大脚奶,千万不敢,千万不敢,我是打比喻,不敢翻案,不敢复辟……
大脚奶说,不行,要想不让我向造反派告你,我要先批判你,把你批倒、批臭才行。
王一虎说,行,你批吧。
大脚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就好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跑掉。你地主富农,解放前吃贫下中农的肉,喝贫下中农的血,你们吃的山珍海味,贫下中农吃的猪狗不如,你们剥削贫下中农,你们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你们穿的绫罗绸缎,贫下中农穿的破烂衣衫,你要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贫下中农绝不答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王一虎,打倒地富反坏右……大脚奶口若悬河,美美地把王一虎批判了一顿。王一虎勾着头,双脚并拢站着像在批斗会上一样。
大脚奶说,王一虎,你向毛主席发誓。
王一虎向着村口塑的毛主席像举起双手发誓,王一虎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地主分子王一虎向你发誓,我绝不翻案,绝不复辟,我有罪,我愿意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这一场精彩的对话,后来一直被人们当作美谈。我曾经问过大脚奶,大脚奶只是笑不说。大脚奶果真被王一虎说中了。二十年后她死了,她死的时候快九十岁了,听到大脚奶的死讯,我就跑到做花圈的地方,让师傅给大脚奶作一双大鞋,作为对她的祭奠,我抱着足有一米长的一双用纸做成的大鞋,到大脚奶家,我把大鞋敬献到她的灵堂前,望着大脚奶的遗像久久地望着,心里默念,大脚奶,你一生是你那双大脚把你害了,你一路走好!
文化大革命前那阵子,各村都有贫协主席,大脚奶可能是苦大仇深,被贫下中农选为我们村的贫协主席。虽说她快七十岁了,不属于队上的劳力,但她毕竟是干部,除过开会,还管村上的一些事。她当时负责我们镇子上的卫生,每天早晨、中午或者下午,她都要从镇子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北头走到南头进行巡视和检查。她检查的时候,嘴里总会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她因为辈份大,绝大多数人都叫她大脚奶。早晨她迎着东方的黎明,朝霞把她染成了金色的,她把东家门敲一阵,骂道,这是哪个狗日的熊娃把尿泼到街道上,比狗尿都难闻。她又去打西家的门,大声骂道,二娃子,你两口子狗日的还睡觉,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还不起来,肯定是昨晚你狗的×乏了,起不来。一时间,里面传出回声,大脚奶,干脆给你找个老汉吧,省的晚上睡不着,起这么早。大脚奶会骂得更凶,她说,我看你大没老婆,给我当老汉吧。她就这样骂着走着。她发现路边队里莲花白上不知被谁尿了一泡尿,她骂道,喂,各家各户都听着,昨晚谁往菜地尿尿,哪女的不怕莲花白把你×了,男的把哪求给烂了去。中午,她顶着烈日或是冒着狂风,走到街上高喉咙大嗓子地喊,各家各户,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注意听着,从今天开始,卫生大扫除,各家把各家门前的杂草铲尽,把自个儿家的苍蝇灭掉,给老鼠把药下好,狗日的懒得不动,全队给你娃开批判会。黄昏,大脚绅士披着一身晚霞又在街上晃荡。她遇见谁家娃娃没洗脸,就会骂几句,你狗日的娃连脸都不洗还当红领巾,嘴都脏成屁股了,脸上的垢痂有一铜钱厚,你是谁家娃。说着强行拉到街东头的涝池边里去给洗脸洗头。那时候没有肥皂洗头膏之类的东西,她就用涝池边的灰草草拧成汁给娃娃们洗头。她碰见谁家娃的衣服脏了,她也会骂一阵。她说,你看你狗日的碎熊,把衣服穿的像牛嚼了,皱里吧叽的,脏得像月娃子的尿布。有时候,村里有两口子吵架,她会凑上去说,狗日的打架的事,硬要吵嘴。指着男的说,你把你媳妇外狗日的往死的打,打死我去抵命,两口子会立即停下来喊她大脚奶,她板着脸说,别叫我奶,我没有你们这丢人现眼的孙子。那一年,我们村里的地主分子王一虎挨了批斗,躲在没人处哭。大脚奶知道后跑去骂,你狗的哭啥哩,有啥哭的哩,你还是地主分子,地主分子叫你枉当了,眼下就是这么个形势,这是搞运动,搞运动不批你斗你,批谁斗谁?有啥哭的哩,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来,不批地主富农,批我们贫下中农不成。几句话说得王一虎由哭转笑。说,任主席,您就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她说,啥任主席,狗屁主席,叫我奶,大脚奶。
听人说,大脚奶就年轻时的容貌,可以嫁个有钱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穿绸子、披缎子,可偏偏是她的那双大脚把她害了。她亲口给我讲过她的身世,她说,她一生下来,她妈就断了气,长到三岁的时候,她爸也死了,她就成了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到了裹脚的年龄没有人经管,她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大脚。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高挑身材,风摆杨柳,毛乎乎的大眼睛能把男人的魂勾去,一双大奶子男人们见了就站不稳。你说,哪个男人不想娶我当老婆,可人家往你脚上一看就摇头走了。她说,旧社会女人家都是一律的小脚,脚越小越好看,书上不是叫三寸金莲吗?那个潘金莲,西门庆就是爱上她的小脚才把武大郎害了,娶她为妻。她说,旧社会女娃十三四岁就嫁人,我长到二十岁还没人要。后来,村里的老光棍陈发祥娶了我,她比我整整大了二十岁,按说,他给我当爸都成,可他那个苦命鬼,把我娶进门不到五年就害了痨病死了。她说到这里,脸上的神情有些黯然和伤悲。她说,都怪我这双大脚,我要是小脚,现在至少是子孙成群,儿长女大了,不像现在孤身一人。大脚奶给我讲到这里,她不愿往下说了。关于她的一些故事,还是后来我几次从大脚奶嘴里讨出来的。
大脚奶说,她三十岁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处女,你知道吗?就是和男人没有睡过觉。她说,她的那个老男人不行,他是个阉驴,不能干那事。不能干那事他就自卑,瞧不起他自己,他连摸一下她都没有。那时候,她年轻,不能干就不干了,可那老男人死了那几年,她有些守不住,白天忙还可以,可到了晚上,她寂寞,女人没有男人的日子难熬。她说,再难熬也得熬,她把一碗铜钱撒在炕上和地下,黑着灯爬下去摸,等她一个不剩的摸完铜钱,夜也深了,她也人困马乏了,不然,她会一夜一夜地失眠。她说那满满一碗铜钱,几年下来,被她摸得明光明光的发亮。
大脚奶说,她三十岁那一年,遇见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叫王树和,四十多岁,人也长得精干。他公开的身份是一个货郎,他挑着一副担子,手里拿着一只拨浪鼓,走村串户的卖货,担子里挑的都是一些针头线脑、五色颜料、洋布袜子和洋火之类的货。他把拨浪鼓摇着“咕咚──咕咚”的响,嘴里叫喊着走东家进西家,就像《红灯记》戏里那个磨刀子磨剪子的人一样。她说,说起来也是缘分,那一天,王树和挑着货郎担子刚走到她家门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王树和跑到她家的门洞避雨,她拿眼睛一瞅,看见王树和被雨淋成了落汤鸡,全身没一处是干的,冷得在打颤,她心里不忍,跑出去把他叫到了屋子里,拿出她那个老男人留下的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天也黑了,雨还在下,王树和也偏偏病了,发开了高烧,昏迷地怎么也叫不醒。就这样,王树和在她家住了三天,他侍候了三天。等王树和病好了那天,王树和拿眼睛瞅她,她也拿眼睛瞅他,这一瞅,瞅出了事,她和王树和过在了一起。
大脚奶说,这都是缘分。这男人和女人找意中中人,你去找,你找不到,全凭碰,她和王树和就是碰在一起的。她说,要是王树和那天不避雨,她就碰不到,就是避雨,不是在她家而是在其他什么人家,她也碰不到。她说,要是王树和没有病,他避一会雨,雨一停,他就会走人,可他又偏偏病了,病得很重,走不了人,就睡在她家,他要是没有病,她也碰不到。她说,要是王树和不瞅她,她也不瞅王树和,她也不会和王树和在一起,可偏偏他瞅我,我瞅他,他瞅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像闪电一样亮了一下,她也感觉她的眼睛也像闪电一样亮了一下。这闪电碰在了一起,冒出了火花,这火花把她的心照亮了,她当时就感觉,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男人,她要找的人就是他,她和他的生疏、陌生一下子都变了,她好似以前就认识这个男人。她说,她当时问王树和,你不嫌弃我脚大?王树和说,不。她说,你愿意做我的男人?王树和说,是。她说,我还没有和男人睡过觉。王树和说,我知道。
大脚奶说,就这样她和王树和成了两口子。白天王树和走村串户的去卖货,晚上回来。就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王树和出事了,他被国民党的民团杀了,民团头子王二虎把他的心肝肺挖出来炒的下了酒。大脚奶说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脸都成了黑的,眼睛里冒着火,拳头捏的咯吧响。我知道,她是仇恨那个王二虎。她说,那一天晚上,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很黑,刮着北风,风把地上的土刮起来乱飞,把树枝吹得摇摆,把家里的门窗吹得哐当哐当直响,她的心有些慌,也有些怕,就在她心慌害怕的时候,那个王二虎骑着一匹枣红大马,领着二三十个民团士兵冲进了她家的大门,还没等王树和穿衣服就被五花大绑押到了三关镇。王二虎说他是共产党的探子。
大脚奶说,现在她回忆起那天的事,她心都疼,眼前就冒金花花。那一天,晚上吹了一夜风,天一明就下起了毛头大雪。天冷得出奇,又接近年关,这一天镇上有集,人特别的多。王二虎把王树和绑在民团院子里的树桩上要进行处决。她说,这处决不是枪毙,也不是砍头,而是王二虎要亲手把王树和的心脏和肝脏挖出来炒菜下酒。王二虎原先是一个土匪头子,后来当了民团团长,这人杀人成瘾,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牛眼睛,一脸凶相,人都叫他牛魔王。她说,那天她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她亲眼目睹了王二虎挖吃王树和的心肝肺的全过程。王树和被绑在一根树桩上,除穿一条裤衩外全身暴露,一个民团士兵端了一盆清水往王树和的胸膛上抹了抹,又拿出一瓶老白干往王树和身上洒了一遍。王二虎拿着一把牛耳小刀,狞笑着向王树和的胸膛伸去,一下就把王树和的肚皮割开一条口子,心肝肺完全暴露在外面,王二虎又噌──噌几下割下了王树和的心肝肺,用刀子挑着放在了他面前的案板上,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做饭师傅,用刀很快地切成了小块,然后下到案板旁的锅里炒了起来。大脚奶说,这过程她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一点虚假都没有,王树和的心肝肺炒好后放在了王二虎面前的饭桌上,王二虎叫来几个民团的小头目,喝酒划拳,把王树和的心肝肺当下酒菜。她说,当时围在旁边的人全都呆了,一齐低下头不敢去看,那可是世界上最残忍、最毒辣的一幕,这情景就像烙铁印在了她的脑子里,永远都抹不去。大脚奶说,当王二虎向王树和下刀子时,王树和不屈不挠大骂王二虎,给王二虎唾了一脸口水,当时他只能这样,他想用手打,手被绑着,他想用脚踢,脚也被绑着,只有嘴没有被堵。当王二虎把王树和的肚皮划开后,王树和先是疼得头上冒着汗,然后脸上的肌肉就扭曲变形,再然后脸就变成了黄的,先从额头一直黄到下巴上,黄的像一张黄表,一点血色也没有了,最后头歪向一边,就在这头歪向一边的时候,王树和还拿眼睛在人群里寻找她,当她刚接触他的目光的一瞬间,王树和咽气了。她说,这一目光也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消失。
大脚奶说,她当时真想从人群中冲出去和王二虎拼命,几个乡亲们硬拽住她的胳膊,她死活都不能动,她想张嘴骂王二虎,乡亲们又用手捂住她的嘴,她同样死活喊不出来。她说,那是一九三五年冬天的事,那一年,她刚好三十五岁。杀害王树和后,王二虎扬言要她给他当小老婆,她被乡亲们藏了起来。大脚奶说,也真是应了古人一句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要不报,时间没到。三天后,王二虎的人头挂在了我们镇的南门上。王二虎的心肝肺同样被炒成菜放在城门楼底下的一张桌子上,一百名民团士兵全部被俘虏。只是那个给王树和身上泼水洒酒的和炒心肝肺的大师傅在杀害王树和后的当天晚上就逃跑了。她说,她知道这一消息,跑到镇子上去看,她望着王二虎那颗人头,把王二虎心肝肺炒成的菜全部吃了下去,然后她就嚎啕大哭。她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也正好镇上逢集。刚才还红日当头,她放开嗓子一哭,刹那间一阵狂风四起,之后又有一股龙卷风,生生的将王二虎的头卷上了天,在空中呼──呼地打着旋转,最后落到了杀害王树和的那根木桩旁。王二虎的人头被摔的脑浆迸流,眼睛珠从眼眶里跳了出来滚了老远,两只野狗三下五除二就将王二虎的人头吃了个一干二净,最后只剩下些头骨。街上好多人都跑来向王二虎的头骨洒尿。大脚奶说,你不信,洒在王二虎头骨上的尿流到镇南面的涝池,一时三刻涝池都淌满了。
大脚奶说,王二虎杀人家共产党的交通员,人家共产党的游击队当然不会放过他,第三天就把他杀了。听了大脚奶的故事,我感到惊心动魄,后来我又查看肖关镇史,果真,镇史上记载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我敬佩王树和为革命献身,仇恨那个王二虎,也对大脚奶的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
就在我和大脚奶见过面之后的半年,大脚奶被红卫兵当作叛徒揪出来批斗,她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木牌,木牌上写着“大叛徒任大脚”。被红卫兵押着游街,别的这分子那分子个个都低着头,唯有大脚奶昂着胸,抬着头,样子很神气,也很滑稽。我亲自观察过一次批斗大脚奶的大会。红卫兵说,只准老实交代,不准狡猾抵赖。大脚奶说,我没有啥问题,交代啥。红卫兵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她说,灭亡就灭亡,省得挨批斗。红卫兵说,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她说,我不是叛徒,我也没有乱说乱动。她说,她和王树和结婚那几年,她根本不知道王树和是地下党,还是交通员,她也没有向敌人告密。红卫兵说,你没告密,敌人怎么知道王树和是地下党?她说,那你去问王二虎。红卫兵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她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后来,我又到街上看到一副漫画,把大脚奶的脚画得比身子还大一倍,用尽了诬蔑之能事。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大脚奶遭到批斗后,尽管表面上表现的很镇静自若,可她内心极其痛苦,她想三十年前她躲过了敌人的劫难,免于一死,今天,她却避免不了自己人强加给她的罪行,这社会怎么啦,阴差阳错。于是,她想到了死,她先是选择了上吊,结果当她刚用双脚把凳子蹬倒时,嚓一声绳断了。她又选择了喝药,她把老鼠药喝了整整一包,可等了半天,她还依然如故,面不改色,心不跳,她意识到这老鼠药是假的。她又选择了跳井,听人说跳井要先下头,她就将头伸向井口,结果两只大脚顶在一起卡在了井口,上不去,下不来。这时,走来一个人,就是那个受到批判的地主分子王一虎,对她说,上来吧,别这样想不开。她说,帮我一次忙,把我的双脚分开。王一虎说,你是嫌我罪还轻,你死了不要紧,把我害了,我也活不成。上来吧,说着把她从井里拉上来。于是两人就在井口有一段对话。
王一虎说,你还叫大脚,你把大脚枉当了,啥路不该走,走这条路。
大脚奶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我不是叛徒,他们说我是叛徒,我冤枉啊。
王一虎说,千不怪,万不怪,都怪你那双大脚,大脚把你害了,害成了这样。
大脚奶说,这话怎么讲?
王一虎说,你要不是个大脚,而是个小脚女人,你长得这么漂亮,这么水灵,不愁嫁不下个好男人。你要不是脚大就不会嫁给那个老男人,也不会嫁给王树和,不嫁给王树和,就不会有人说你是叛徒,没有人说你是叛徒,你也不会去跳井,去喝药,去上吊,对吗?
大脚奶不语。
王一虎说,要我说,这都是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还是好好活着吧。
大脚奶不语。
王一虎说,你说你冤枉,老子我比你还冤枉,他们凭啥收了我的地,分了我的房,还要批判我。
大脚奶像蝎子蛰了一下,猛跳起来。大声说,王一虎,你想翻案,想复辟?我要向造反队告你。
王一虎吓得连连告饶,大脚妹,大脚奶,千万不敢,千万不敢,我是打比喻,不敢翻案,不敢复辟……
大脚奶说,不行,要想不让我向造反派告你,我要先批判你,把你批倒、批臭才行。
王一虎说,行,你批吧。
大脚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就好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跑掉。你地主富农,解放前吃贫下中农的肉,喝贫下中农的血,你们吃的山珍海味,贫下中农吃的猪狗不如,你们剥削贫下中农,你们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你们穿的绫罗绸缎,贫下中农穿的破烂衣衫,你要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贫下中农绝不答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王一虎,打倒地富反坏右……大脚奶口若悬河,美美地把王一虎批判了一顿。王一虎勾着头,双脚并拢站着像在批斗会上一样。
大脚奶说,王一虎,你向毛主席发誓。
王一虎向着村口塑的毛主席像举起双手发誓,王一虎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地主分子王一虎向你发誓,我绝不翻案,绝不复辟,我有罪,我愿意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这一场精彩的对话,后来一直被人们当作美谈。我曾经问过大脚奶,大脚奶只是笑不说。大脚奶果真被王一虎说中了。二十年后她死了,她死的时候快九十岁了,听到大脚奶的死讯,我就跑到做花圈的地方,让师傅给大脚奶作一双大鞋,作为对她的祭奠,我抱着足有一米长的一双用纸做成的大鞋,到大脚奶家,我把大鞋敬献到她的灵堂前,望着大脚奶的遗像久久地望着,心里默念,大脚奶,你一生是你那双大脚把你害了,你一路走好!